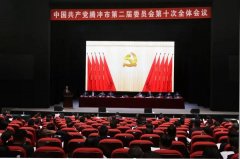|
走过村庄,点点处处,你几乎能一路寻找到那些早已随风飘散了的母亲的眼泪、叮嘱,那些男儿强忍在喉头的哽咽,那些在香案前默默许下的、永远没有说出口的祝愿。男人出门之前,先要去宗祠祖坟和祖先牌位前磕头,告慰祖先这个家又一个男人成人了,他要担起做男人的担子,外出去谋生了,他不会辱没先人的。 按惯例,出门头一天还要到村后的中天寺烧香,烧一串元宝纸火,求观音菩萨保佑一路平安,无灾无病;有的还要抽签卜卦,聆听僧人教诲。到出门那天清早,全家人一起到财神殿拜祭财神爷,祈求财源广进,一本万利,兴家立业,过上殷实的日子。如果愿望得以实现,今后一定要回来还愿,那就是除了敬香放爆竹之外还要给财神爷唱一台大戏,经谢庇佑之恩。 如今财神殿对面的戏台仍然还在,可锣鼓声已经远去,但从戏台建筑的格局与精致,我们依稀可以想象当年热闹兴盛时的情景,可以想见唱大戏的人家脸上的笑容与风光,可以想得出男儿家还穿着开裆裤在唱戏的人堆里串出串进时,心里就种下的的对衣锦还乡的这份风光的憧憬。祭完财神,家人亲友已经在偏房里摆下送行酒,酒席上又是一番千叮咛万嘱咐。此后,就在财神殿前上路。家境好点的,亲人将你扶上马,以示最后扶你一把,从此以后就靠你自己去闯天下了。那块被磨得油光闪亮的上马石,至今仍在财神殿前,见证着那些离别的眼泪和辛酸。 从这里走出去的不远就是出门人叫的“隔娘坡”了。站在“隔娘坡”前,我总有无限感慨,一个村庄的人怎么会取出如此朴实形象、伤感凄楚而又理性实在的地名。显然只有深刻地理解“走”所意味的分量,穷尽了个中滋味的人们才会对着它——对着这蜿蜒着古道又缠绕着决绝之情的地方喊出“隔娘坡”三个字来的。 站在“隔娘坡”前,我眼前总是复现出一个场景:没有尽头的路单调而又漫长,亚热带燠热的阳光下只有旅者在寂寞地往前走着,背影被太阳拖长,缩短,又拖长……路边肮脏的小摊、卖唱的瞎子伴着低哑的二胡拖长声音,哀哀地唱着家乡那个人人都会哼几句的《阳温墩小引》: 起身时 在堂中 忙忙叩首 一家人 话难说 气哽咽喉 抛父母 别妻子 吞声独走 众亲友 同送到 官坡路头 (又叫隔娘坡) 官坡头 好一似 阴山背后 过此地 把家乡 一概全丢 …… 隔娘坡,隔娘坡,不仅标识着亲情痛伤别离,更意味着一种“精神断乳”。 这个村前还有段叫“发财路”的大道,寸氏老人告诉我,他远走夷方的时候家里的老辈专门领他到这里,指着这个地方告诉他:“发了财的人,当了官的人,将来从‘发财路’的大道上光光彩彩体体面面的回家;挣不出名堂的,无脸见人,只能等到天黑了,从山后的小路偷偷摸进家,在外边你随时随地要想想你二天到底咋个回来法。”和顺人把那种贪妻恋子不愿意出门,不敢“走夷方”的男人称为“嘎人”(意即窝囊、无出息之人)。寸氏家族中有个叫寸品生的,自恃考了个秀才,觉得自己算是个有身份的人,逢人便说“我是有顶子的人”,不愿意出门,媳妇便把他的顶戴蒸在橧子里,到吃饭的时候就端出来摆在他面前,寸品生无可奈何,只好去缅甸八莫。 这一切使我想起,在地球北纬接近极地的地方生活着一种极为美丽的列那狐,冬天来到以后母狐就要把新生的小狐赶出家,让它从此独自觅食,学会生存。我看过学者们拍的那个片子,时至今日,也忘不了幼狐在冰天雪地里孤独的嗥叫和母狐走走又回头时眼睛里流露出的凄然又决绝的神情。 说起来,哪个妻子愿丈夫远离家乡,自己留守空门呢?自古到今,那些旷男怨妇、孤男寡女长离别、长相思的凄楚哀伤的故事还少吗?和顺女人守活寡的凄凉是远近有了名的,滇西民谣里都唱着“有女莫嫁和顺乡”,自然是不愿女儿家去受这个苦。秀才妻子硬着心肠把丈夫逼出家门的行为有悖常理,但却明白无误地表现了当地人“走夷方”的价值取向,当这种价值取向发展到一种绝对的统治地位时,我们看到了与此同时产生的一种负面效应,即对人性的一种压抑和曲扭。在这个村庄世代人“走夷方”的生存方式中已经建立起了整个社区“走”的生存观念和习俗。在这种有形无形的肯定和鼓励下,和顺男儿一年接一年地走,一代接一代地走,痛苦却又毅然决然地走。他们相信只有走才有希望,才走得出生路,走得出奔头。这个村庄的人实在是把握住了扩大自身空间、增加人生机遇的要诀。 |